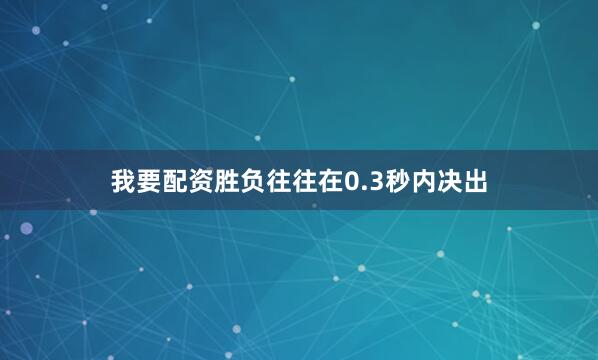来源:民间传说[部分内容摘自《郑志胜回忆录》]
作者:韩福东
郑思群之逝,相较于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更显早逝。(详见:文革卞仲耘之死真相1966年8月2日凌晨,松林坡专家招待所内,这位被工作组定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重庆大学的校长,竟以剃须刀割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血迹斑驳满墙”,电机系学子郑志胜于当日晚餐后,听闻此等骇人听闻的消息,便匆忙赶往招待所,欲一探究竟。
遗体已彻底消失,现场被水冲洗得一尘不染。郑志胜双腿无力,险些失去平衡,踉跄着往回走,直至抵达重庆大学二舍外的“思群广场”旁的水冬瓜林。夜幕低垂,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关于郑校长辉煌历史的传说亦在耳边回响,他不禁黯然神伤,默默哭泣了将近一个小时,泪水浸湿了双眼,以至于看不清前方的路,他踉踉跄跄地摸索着回到了宿舍。
“郑思群被判定为‘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者,背离人民’。我怎能像失去亲人那样悲痛?那只是‘立场分歧’罢了。因此,那时的哀伤,当时并未被外人察觉。”
四载之前,郑志胜与我相对而坐,谈及“文革”时期重庆的武斗盛况,我依旧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胸中激荡的情感。郑思群之死,实为自尽而非遭受殴打,然而随后在重庆展开的暴力事件,其激烈程度远甚于卞仲耘遭遇的北京之变。在武斗最为激烈的时期,郑志胜日复一日地承担起掩埋尸体的重任,因此,他赢得了“尸长”这一称号。

在武斗爆发之前,重庆大学的学生群体中派别之见已显现得尤为突出。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郑志胜,坚定地站在了支持校党委的阵营之中。他的个人经历,映射出革命浪潮中个体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然而,这一切最终均将被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黑洞所吞没。
1962年,郑志胜踏入重庆大学的大门。不久后,他与校长郑思群有了初次相遇。那天下午,正值课外活动,郑志胜身着打了补丁的衣衫,一只有大脚趾外露的破旧胶鞋,坐在团结广场的栏杆旁与同学们闲聊。此时,几位从党委办公室走出的身影中,一位年过半百、身材魁梧、清瘦、衣着简朴的老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朋友,你是新来的新生吗?”
在确认了他的班级信息,并向身边的教师低声提及了几句后,那位老人便悄然离去。郑志胜好奇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出神,这时一位老校友向他透露,那位长者正是校长郑思群。身为“黑五类”成员的郑志胜感到既受宠若惊,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翌日,学校的总务长林先生特地派遣了一位教师送来了一双崭新的绿色解放鞋。这份意外的关怀让郑志胜感动得眼含热泪。
他对郑思群的敬仰由此而生,以至于在“文革”爆发之初,他毅然决然地站上了“保守派”的立场。

重大学子(网图)
据郑志胜所述,1966年6月8日,重庆市委派出由张中玉、张海亭担任组长的首个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旨在协助学校党委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郑志胜当时所在的电机系67级电力一班,以黄顺义为首的部分同学对校党委压制民主、阻挠“文革”进展表示强烈不满。为此,校党委派遣岳崇兴前来征询意见,意图平息初露端倪的革命热潮。然而,黄顺义与岳崇兴之间的辩论异常激烈,令岳崇兴陷入尴尬境地。
随后,校园内的大字报栏上赫然出现了“摒弃校党委领导,独立发起革命”的口号。郑志胜与同学陶森林就此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认为,党中央是由众多地方党组织构成的,而大部分地方党组织表现良好。若所有基层党组织的根基动摇,党中央岂不成了无源之水?陶森林便提笔书写了“誓死捍卫校党委绝对领导地位!”的标语,而郑志胜则购置了长达二十多米的电线,将其悬挂于宿舍楼旁的道路上,并在那里进行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
在演讲中,郑志胜详细列举了郑思群校长对学生关怀备至、生活简朴、廉洁自律的诸多事迹,并对同学黄顺义提出了“野心勃勃”的指控。他以达县渡市“四清”运动期间为例,指出黄顺义当时担任三星大队工作组的一员,却对工作组长持反对态度,导致组长无法施展工作,江泽佳主任因此特地要求他们与地方干部加强团结。
此指控根本站不住脚。郑志胜已坦白,黄顺义当年之所以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实因他对工作组为排查“四不清”干部而采取的过于严厉、无限上纲的做法表示不满。在这起事件中,黄顺义的行为体现了他“坚守正义、捍卫真理”的立场。
在演讲进行之际,电机系二年级的两位女生并未屈服,她们与郑志胜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结束后,她们更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发出警告:“郑志胜,请你切勿轻举妄动!”面对嘲笑和围攻,郑志胜依旧勇敢无畏。尽管如此,他也赢得了部分同学的理解与支持。

重庆大学图书馆
工作组初抵重庆大学时,校园内呈现出一片混乱景象。原有的权力核心——大学党委,正面临清算的命运,而工作组则象征着新的革命方向。学生们也纷纷被卷入了这场斗争的风暴之中。随着郑思群被停职,重庆大学党委的权力逐渐旁落,郑志胜所属的派系迅速陷入了尴尬境地。他原本已经接受失败,甚至曾对自己针对黄顺义的言行进行了检讨。然而,郑思群的离世激起了他的斗志,恰逢毛泽东作出撤销工作组的指示,他从8月3日起便投身于驱逐重庆大学工作组、推翻“黑市委”的斗争之中。原本支持大学党委的“保守派”如今转变为“造反派”,而那些支持工作组的革命群众,许多则坚定地站在市委一方,成为了“保守派”。
固然存在特例,如黄顺义,他始终秉持着推翻权力核心的叛逆精神,从抵制重要党委的决策直接转向反对重庆市委,进而成为新派造反组织的领军人物,即“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核心成员。派系之间的斗争,其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郑思群离世三天之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遭受一群学生的袭击,最终不幸丧命。(详见:王晶垚论卞仲耘案“革命并非如请客吃饭那般闲适……它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激烈推翻的举动”,此言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重庆大学工作组尚且得志的时期,一位名为孙育福的同学曾协助郑志胜研读毛主席的三大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以及《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旨在确立对于“革命”与“造反”的准确认知和坚定信念。
鲜有学生能完全置身于政治运动的浪潮之外。“文革”爆发之前,掌权者往往与血腥或压迫的帮凶之嫌难解难分。一旦群众运动兴起,革命青年们便轻易找到了将当权派推倒在地、进而踩上一脚的充分理由。以中国西南地区为例,李井泉的权力地位尤为典型,他需为“大跃进”期间四川省千万民众的困境承担责任。若非“文革”中的暴力狂潮,他恐怕会愈发得到中央的青睐。

李井泉
然而,这场失控的暴力盛宴,终究将我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校园内的青春躁动,在政治人物的有意操纵下,发出了一曲在人肉祭坛上激昂的号角。
在1966年“11·13”大会假检查结束后,李井泉随即退隐幕后,沿成昆铁路逃离。次年一月初,他乘坐飞机逃至上海,企图躲避革命群众的斗争。然而,在元月十八日,他遭到重大8·15同学郑全体、吴成金、赖民国,以及西南局办公厅干部周仁佑、何锦沐的联合行动,被“揪”回成都。随后,于元月十九日,李井泉被郑全体等人带回重大8·15总团。自此,他便在重大8·15居住,直至四月下旬方才离开。
这段文字出自重庆大学造反派组织于“8·15”事件中所撰写的《“智擒李井泉”真相的初步调查》一文,该文档至今完好地保存在重庆大学的档案库中。此篇纪实文献生动地再现了革命青年与敌对势力斗智斗勇的激烈过程。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在历史的长卷中,关于李井泉的记载,相当一部分内容将围绕着那场三年饥荒展开。(参见:)四川老干部回忆李井泉在1958年至1961年间,四川省经历了连续四年的人口锐减,净减少人口达到622万。在全国范围内,仅有河南省的人口减少程度可与之相媲美。然而,在1962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被特别指出为重灾区的省份仅有河南、安徽、甘肃及青海,而四川则顺利避开了这一标签。当时,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因故被刘少奇降职使用(详见相关资料)。尹曙生:曾希圣如何掩盖饥荒),即便如此,李井泉依旧我行我素,自称为“西南王”。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虽未直指其名,却对李井泉进行了隐晦的批评。然而,驻川中央领导却转变策略,将火力从集中抨击李井泉转移,引导与会者进行自我批评。(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张素华,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
在文革爆发之前,我国历次政治运动均以人治为主导。这一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文革时期造反学生的心理状态至关重要。当权派遭受批判,若撇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意识形态标签,亦非全然无据。李井泉因在大饥荒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备受指责,而作为老革命家的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亦然——尽管他的处境可能更为复杂。关于郑校长的艰苦朴素,后世多有所忆,然而,这一面只是硬币的一侧,另一面则需要将其与建国后高校整风运动几乎未曾间断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深入考察。
反右时,反对党委和党支部就是反对党中央。文革则是完全不同的套路,直接冲击的就是党委和党支部。在重庆大学,郑思群6月中旬即受到学生们的攻击。电机系郑志胜最早是在学生三舍外的大字报专栏上看到冶金系四年级学生贴出的大字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石圆台上演讲的学生,对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慷慨激昂宣示郑思群的罪状。
此刻的局势已变得一片混乱,众多如郑志胜般坚定支持郑思群的学生,与冶金系学子展开激烈辩论,要求对方出示确凿证据。据郑志胜所述,曾有一位名叫佘某的同学承诺在48小时内公布“郑思群是黑帮的钢鞭材料”,然而最终未能兑现,竟将证据藏匿于重大冶金馆的楼顶。支持郑思群的学生并未就此罢休,他们持续前往佘某的宿舍进行骚扰,导致同宿舍的室友夜不能寐。为了求得片刻安宁,室友们只能将一张写有“我不是佘**,请勿打扰”的大字报覆盖在身上。
6月17日,针对郑思群的批判大字报被张贴出来,翌日午时,重庆市委工作组便抵达重大校园,擅自取代了党委的职能。这场较量异常激烈,数千名学生,无线电系学生尤为突出,他们在校内彻夜进行示威游行。郑志胜亦投身其中,积极抵制工作组,坚定地站在校党委一边。
这之间的是非怎么论断?一些文革史家对派驻工作组持基本肯定意见。其实哪有这么简单。以重庆大学为例,工作组进驻后,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学生6月18日的示威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件是令郑思群停职在操场面对全校师生公开检查,并最终将其逼死。再以北师大附中论,卞仲耘之死与其说是革命学生对工作组派驻的一种反弹,毋宁说是对其批判卞仲耘路径的一种延续。这中间本来就是一团浆糊。

先前提及,在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当权派往往难以摆脱跟随极左路线的从属角色。这种评价固然基于事后的评价标准,然而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价值评判体系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工作组被派来主导运动的方向,随之而来的自然不免派系间的争斗,最终亦不可避免地导向对所谓的“黑五类”的批判。
以广场狂欢的方式,由学生和群众发起革命,往往会使运动失去秩序,然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地方权贵,诸如李井泉等人,似乎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接受惩处。即便在所谓的“工作组模式”下,他们依旧掌握着操控权,并从中获益。若回溯到文革初期那段语境,依旧混乱不堪。这场冲突实为一场内战,我们对于当权派在文革中的遭遇进行评价时,至少应当将其置于新中国建立前30年的整体历史背景中进行全面考量。
重返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离世之案,自8月3日他选择结束生命以来,仍有学子们张贴大字报,为他鸣不公之冤,甚至有人对其死因提出质疑,疑其遭受暗杀。传闻中,凶手逃离现场时,在围墙上留下了脚印与血迹。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成长的郑志胜,地主出身之子,不禁回想起中美合作所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以及杨虎城将军被杨进兴所害的悲剧,深感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他当时坚信,郑校长如同杨虎城一样,最终被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类似国民党对待杨虎城的方式,秘密杀害。在郑思群被工作组停职后,他压抑、沉默了一个多月的激情,终于在那一刻如同火山般爆发。
随之而来的是显著的变化,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当权派主导政治运动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理念的深入人心后,红卫兵群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地方权力中心的多元化趋势,使得武斗的风云席卷了兵工厂林立的重庆。在日复一日掩埋尸体的工作中,郑志胜亲身见证了这场运动的顶峰时刻。
正规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股票配资炒股网而不是“让你自己感到很用心”
- 下一篇:没有了